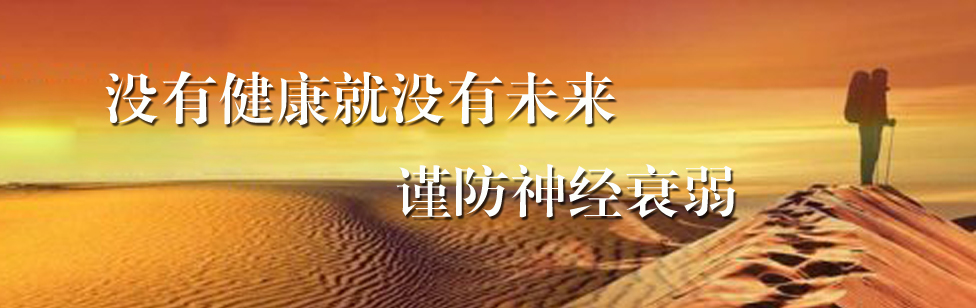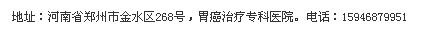理想国imaginist
《卡夫卡是谁?》
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的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曾写下《变形记》《审判》《城堡》等揭示现代人类面临困境的小说。在他笔下,现代社会充斥着被异化的人与繁冗的官僚程序,人们面临彼此间的隔阂,忍受冷漠的人际关系,最终将自己变作一枚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焦虑、迷茫、病态之中完成短暂的生命。
卡夫卡的小说也被认为带有预言的特质,他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纳粹德国的官僚系统运作,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似乎都应验了他作品中揭示的未来,甚至直到21世纪,我们仍能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某些真实的社会缩影。这位一生都不曾找到灵魂归属的失败的“异乡人”,留下的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忧虑。虽然他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始终感到迷茫,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他的犹太民族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写作。
卡夫卡的犹太属性
节选自[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
01.
卡夫卡的犹太特性作家(writer)卡夫卡,当然还可以作其他分类。出于这样的目的,深入地研究一下他的犹太特性(Jewishness)将不无助益,不过只就它与其写作的关系而论,不作他的人格或他的神经衰弱症而论。犹太特性在他的艺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堪比法国特性(Frenchness)在福楼拜(Flaubert)作品中的角色,只不过,在福楼拜的艺术中,法国特性是一种既定的条件,而犹太特性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条件,只限于它作为其主题出现的范围。就犹太人的条件(或犹太人的境况)成为卡夫卡艺术的主题而言,它形成了其形式——成了内在的形式。通过他的诗(Dichtung)——字面的意思是,他的想象和沉思——卡夫卡在犹太人被驱逐的命运中获得了一种关于犹太人境况的极其生动的直觉,以至于将有关它的表达转化为它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种直觉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在风格上和意义上都成了犹太式的了。
卡夫卡的小说与散文诗看上去非常有特质,这既由于它们是犹太人写的,也由于它们是他写的。它们是我所知的唯一一种在现代非犹太语中感到悠然自在的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文学艺术。与海涅(Heine)不同,卡夫卡不需要为了拥有德国人的特性而出卖任何犹太人的自制。然而他的陌生在德语中并不比克莱斯特(Kleist)的叙事散文更陌生(也就是说,卡夫卡的散文也许道出了更多关于德国人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卡夫卡自己的东西)。卡夫卡真正的陌生在于他的形态,他关于时间、地点、运动和人物的虚构——而不在他的修辞。在这些形态中存在着亘古不变的要旨,他的艺术的趋势。
《卡夫卡》
在卡夫卡那里,时间的运动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小说作者都不同。他的主角生活在对早已作出的决定,早已确定的结果,而非生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决定、结局与判决,并不总是准时来到,因为它们总是在场的。一切似乎都早已在很久以前签署、封缄、传递,只是这个很久以前存在于某个神秘的向度,在那里一切都同时发生,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是这一向度,伴着它对近与远、辉煌与单调、绝对与直接、永恒与瞬间的融合,从四面八方向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渗透。卡夫卡散文的独特调子回应着这一向度。
在这一调子提高的少数几个场合,只有在雄辩中,他才是反讽的——在那里,事实似乎需要某种总结,而这种总结对于这些事实来说永远是不充分的。卡夫卡似乎想要抓住与眼下的情势相关的一切东西,但是这一相关原则总是在躲避他,而他小说的运动——就其确实有所运动而言——可以说更多地存在于对这一原则的不断寻找中。在他似乎总是渴望着透明与神秘的通缩之时,他反复拿捏的原材料到最后总是与最初一模一样:这是一种似乎不能为理性的心智所穿透的相似性的组织(tissueoflikenesses)。
卡夫卡的小说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依据时间、地点、历史、地理甚至神话或宗教的客观坐标来加以定位的。数据都不是从推理而得,它们干脆就是给定的,就像在童话或是在《一千零一夜》(theArabianNights)里一样。其秩序亦然,存在于重复中。卡夫卡的普通主角被托付于,同时也屈服于日常生活,但是故事——事实上也就是卡夫卡的艺术——却只始于日常生活的毁坏,并且主要通过重返日常生活的努力向前发展,这一日常生活本身也试图将毁坏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行动主要存在于各种从来无法精确符合情势的假设的形成、阐发及其放弃之中;仿佛正是现实的趋势和现实的纹理本身在反驳它们。
02.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与我们的梦幻世界之间的相似性早就有人说过了,而且说得很好。然而,要想证明我们在别的地方找寻这种相似性是正当的,却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毕竟,我们在梦里并不怎么喜欢推理。稍微熟悉一下犹太人的传统就能暗示另一种排除所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只要你朝它看一眼并愿意继续求索下去。卡夫卡的主人公们在其中找到其唯一安全和可认知现实的日常生活与逻辑的单调乏味,或者毋宁说合理性的单调乏味,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过扭曲的还是未曾扭曲的)都与所有遭驱逐的犹太人两千年来一直在寻找其形状、身份及其生活安全感的体制相似。我是说那个被叫做《犹太法典》(Halacha)的法律体系以及由这个法律体系确立起来的精神活动。
这部法典是为覆盖虔诚的犹太人的全部生活而设计的,它是行为准则和仪式法则的逻辑推演,而且是通过代代相传,经过“口头法典”(theOralLaw),从Pentateuth,亦即“成文法典”(theWrittenLaw)或“神谕”(Torah)那里推演而来。犹太法典通过将日常生活中注定会愉悦上帝的东西包括进来,从而使人类生存神圣化。它不仅使道德法典化了,而且还通过将行动和言词的仪式化的重复编织进日常生活,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以超越实践意义的东西;行动和言词的不断重复可以将日常生活的肌理直接或间接地与神,以及被隔离的过去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过去中,上帝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之间的协议确立了法律并“创造”了历史。
《卡夫卡》
对生活在传统中的犹太人——亦即正统犹太人——来说,历史在两千年前巴勒斯坦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中遭清洗而停止,而且不会重新开始,直到由弥赛亚来重建这个国家为止。与此同时,犹太人的历史存在也遭到悬搁。在流亡状态中,犹太人生活在远离历史的处境中,生活在犹太法典的“篱笆”或“中国长城”背后。走到“篱笆”另一边去的历史是渎神的历史、非犹太人的历史,更多的属于自然史而非人类史。因为它并不涉及与神的交接,因而没有任何真正的新意。这种历史在最好的情况下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对其神圣的日常生活或其生理存在将构成一种威胁。真正的历史将会以真正的新意重新开始,只有当犹太国家再次屹立在直接与上帝交接的位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内,非犹太人的历史开始以一种通过“解放”犹太人——意思是“教育”并将他们重新吸纳为国民的新方式介入被驱逐犹太人的生活。但是其结果并没有使得非犹太人历史更少敌意,无论是对正统犹太人还是对已归化的犹太人。确实,非犹太人历史,对已归化的犹太人来说变得更为有趣,不过这并没有使它变得更为温柔或更少成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因此,被解放的(或自由)犹太人仍然必须诉诸犹太法典式的安全感和安稳感,或者毋宁说无需再流浪的某个版本。如果这种新的犹太法典不能从宗教权威那里推导出来,那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向来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典型——就不得不带着种种可怜的关切,在此地和当下的教区生活。日常工作、谦卑、清醒,作为自己的目的,为它们自身的缘故,以及纯粹出于安全感考虑,得以结合在一起。
这种新的、世俗的犹太法典排除了犹太人的过去。它承担着对未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人们对任何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