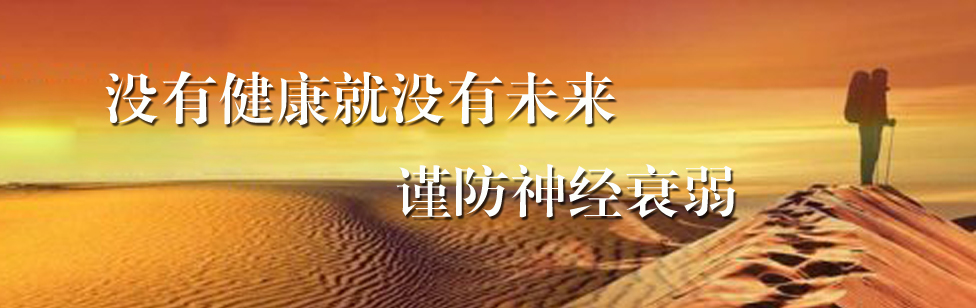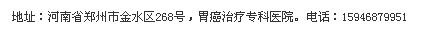昨天贴错了照片,非常抱歉,再传一次。
夏目漱石的神经衰弱
应杰
“神经衰弱”一词简直就与夏目漱石形影相随。只要一提起夏目漱石,似乎接下来马上能想到的,就是他的神经衰弱。在他最为人知的肖像照(见图一)中,夏目漱石臂戴黑纱(当天是明治天皇出殡日),满脸倦容,右手托着太阳穴斜靠在椅背上,仿佛正隐忍着神经的刺痛折磨。千元日币上的漱石肖像画,虽然看上去正襟危坐,但却显得忧心忡忡,其思绪像是飘落在遥远的彼方。而夏目漱石唯一一张面带笑容的照片(见图二),是在杂志记者三番五次恳求之下才拍摄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强颜作笑”罢了(《玻璃门内(硝子戸の中)》二,)。
夏目漱石的神经衰弱似乎在留学英国期间达到了顶峰。年,按当时习惯已是年届中年的夏目漱石去往英国研习英语与英国文学。在留英第一年,夏目漱石尚且通过私人导师多少与外界保持联系,到第二年,夏目漱石开始闭门谢客,沉湎于“什么是文学”的探索之中。随着孤独的加深,夏目漱石逐渐显得焦躁不安,以至不吝在日记中对英国、对英国人恶语相向。有人好意邀请他至家中喝下午茶,他却写道“邀请从未谋面的外国人而且是日本人到家中做客,真是野蛮。(……)聊几句套话(……),早早告辞。太浪费光阴了。西洋社会愚蠢之至。如此乏味的社会是谁建的?有意思吗?”(笔者译)
留学英国给夏目漱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即使回国数年后,他依然在《文学论·序》()中表露出愤懑之情:“余寓居伦敦两年为最不愉快之两年。于英国绅士之间,余如一条与狼群为伍之犬,生活郁郁寡欢。闻伦敦人口有五百万。余不讳言,余当时之状态,如五百万滴油中之一滴水,叵且维系露命。”(林少阳译,下同),甚至宣称“若以己之意志,余当终生不踏入英国一步。”
把夏目漱石的神经衰弱归因于文化冲突(cultureshock)是最为简单的办法。比如平川佑弘就认为“文明的差距令夏目漱石愕然,加上内心非西洋的纠葛,以及作为落后国民所感到的过度自卑和不安”是夏目漱石神经衰弱的起因,而河部利夫则批判“不踏入英国一步”的说法是“写得太任性,只能说明他的自私或者幼稚无知。”
留学经费的不足导致夏目漱石生活拮据,西欧发达的工业文明乃至因个子矮小而感到的人种自卑等等因素,的确给夏目漱石带来了过不少的困扰,但是把他的神经衰弱仅仅归因于文化冲突或者认定他的留学失败却有点过于表面化。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过于相信既善嘲笑又善自嘲的夏目漱石留英日记的缘故。
其实在《文学论·序》的后半部分,夏目漱石透露出了很多的解读密码。
“归国后的三年有半,亦不愉快之三年有半。然余为日本臣民,不能以不愉快为由而离去。(……)余之意志以上之意志命令余:为支持日本臣民之荣光与权利,务必避免一切不愉快。”
留英的二年固然不愉快,但是回国的三年半“亦不愉快”,只不过作为日本臣民,无法像逃离英国那样逃离日本,是逃无可逃而已。想要逃离的原因或许各异,但作为一个想要逃离的对象,英国也好,日本也罢,并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差别。
夏目漱石曾经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无良的世道捉弄人。居心不良之徒目中无人,且恃众为所欲为。我不想再待下去了。去乡下享受更为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我的最大目的。可是到了乡下,发现原来那里和东京同样令人不快。”(,笔者译)
在这段话中,夏目漱石道明了远离东京去往松山,又从松山去往熊本的缘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逃离吗?而恰恰因为发现日本的乡下也和“东京同样令人不快”后,他才起了留学英国换句话说是逃离日本的念头。他在《文学论·序》中所说的推辞留学的说法,不可尽信,那不过是他想让文部省批准自己学习英国文学专业而非英国语言专业的一种抗争而已。在去往英国的客轮上,他所吟诵的俳句“秋風の一人を吹く海の上”,才真正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逃离日本后悠然自得的内心。
逃离、逃避、逃亡,这些词汇构成了夏目漱石文学以及人生的关键词。
年,为了发动对外战争,明治政府实施了征兵令。同年,夏目漱石为逃避兵役把户籍寄往了北海道。在不久后的年,便发生了日本侵华甲午战争。
年,长野县一所小学发生火灾,烧毁了明治天皇的“御真影(油画肖像画的翻拍照片)”,校长引咎切腹自杀。此时作为万世一系的权力总揽者,天皇已经确立起绝对权威,日本全国中小学都设立了安置“教育敕语”以及天皇肖像的值守室,课前背诵敕语,向天皇像鞠躬行礼成了必修环节。而夏目漱石却在年出版的《哥儿》中,描写了主人公如何置值守室于不顾,偷跑出去泡温泉的情节。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全日本上下一片赞美庆贺声中,夏目漱石又在《三四郎》()中借出场人物之口说:
“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日本也会渐渐发展吧。”(……)
(……)“将会亡国呢!”(吴树文译)
“将会亡国”,这是夏目漱石对日本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警告。虽然日本有了坚船利炮,有了汽车铁路,也学会了西装革履,甚至是议会制度等西方文明的外表,但是作为现代文明根本基础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内核却在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最终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潮流中一点一点地丧失殆尽。所以夏目漱石将现代日本的开化称作为“外发式的皮相开化”(《现代日本的开化》,),终有一天,这样的开化会毁灭日本。他去往英国留学的目的,并非徒学英国之表,而是要在作为西方文明结果的偶然中发现日本现代化的必然。他对英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感,恰恰是他对日本“外发式开化”的批判。
日本的现实却令夏目漱石失望。在几近绝望之中,年他在学习院大学,面对贵族子弟们做了一次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说:“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国家道德比起个人道德来,要低几个层级。(……)我认为,在国家安稳之际,更加重视德行更高的个人主义,是理所应当的。”
如果因为夏目漱石说过“则天去私”就称其为“高踏派”及“余裕派”,或认为他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而逍遥自在,那是对夏目漱石最大的误读。正如他本人所说“但凡余身边状况不变,余之神经衰弱与颠狂应与生命同在。”那样,就是在这种逆时代潮流的苦闷之中,在与“余之意志以上之意志”的抗争中,夏目漱石陷入了身体逃离、精神逃亡的痛苦分裂之中,这才是夏目漱石神经衰弱的最根本原因。
夏目漱石的神经衰弱最终未能阻止日本走向疯狂,当代的日本是否还有夏目漱石这样的神经衰弱?
应杰老师往期力作!
高年级“高”在何处
熊与“核能”
《最后一课》的背后
クマ?くま?熊
沙拉纪念日
天气预报与手冢治虫的阿童木
夏目漱石的户口
舌尖上的日本
应杰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