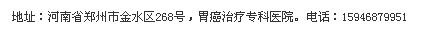他走了,低着头,那么低,背着行李,那么沉,穿过公路,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回头望了我一下,转过身去,默默地向前走着,眼也许在流泪,但心却一定在流血。望着他那低沉的头,此时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新溪一中时,他的头就低着,可没这么低,难道他的头以后永远如此?
上街买了点儿东西,我沿去学校的三百多级台阶上行,中途小憩了一下。转身向下一望,只见一个人背着行李,正顺级而上,大概是一中的学生,说不定就是我班上的呢。看他很瘦小,也好像有些累,手里却还拿着一本书。难怪教务处副主任说这里的学生学习很刻苦呢。他慢慢走过我身旁,我一瞧,哟,居然还是本英语书。大概是由于职业的偏见吧,一种快意促使我“哎”了一声。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先是一怔,然后笑着说道:
“啊,铁平哥,是你,你分到一中了吗?”
这声音多熟悉啊!可这容貌多陌生啊!但这称呼使我认出了他。
“举人,是你!我的天啦,认不出来了!”
的确,我怎么认得出他呢?他已早生华发,头发上像蒙了一层灰,几条抬头纹过早地出现在他的额头上,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脸色黄里泛黑,眼神也有些忧郁,已全然不是叫我铁平哥时的模样了。
我们一起来到我的宿舍,在路上他告诉我今年他上高二了,明年七月就要参加高考。
“铁平老师,以后我可以来这儿做功课吗?”
我欣然答道:“当然可以,我可以给你一把钥匙,我不在你也可以来。”
他竟站了起来,感动地对我说:“太感谢你了,这回有希望了。”
“你是复读的?”我一听“这回”二字,就问道。
他那本来充满感激和希望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变成了诧异,进而成了羞愧,脸渐渐地红了,头渐渐地低下了,喃喃地“嗯”了一声。啊呀,我真不该问这个问题,但为时已晚。我连忙表示歉意,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我只好给了他一把钥匙,叫他先去休息。此时他才慢慢地抬头,眼睛忽闪了一下,闪着一种与他刚才的表情不相称的光,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他点了一下头,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走了。他眼睛中那瞬间的光亮才使我回想起他少时那双给我很深印象的眼睛。我们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知青来到了新溪县范家坪接受再教育。村头站着大部分村民,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围观。我望见人群中站着一个穿得较破烂的十岁左右的孩子,那眼神似乎很奇特,是那样有神,虽略显瘦弱,但眉目清秀,脸蛋也还有点白,的确很是可爱。毫无疑问,他是富有天资的。
我被安排在老篾匠范功贸家住,来大队部接我的,竟是那个男孩。我问他叫什么,他笑着答道:“范进。”我怀疑我的听觉神经开了小差,又问了一遍,他还是笑着说了一遍,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站了起来,让范进站在板凳上,忍住笑对伙伴们说:“大家静一静,听这个男孩自我介绍。”范进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微笑着用那甜甜的童音,毫不畏缩地说:
“我叫范进,模范的范,进步的进!”
“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高声喊着“举人”,“举人”。自此大家就叫他“举人”了。
“铁平哥,你会翻跟斗吗?”月夜,范进眨了几下他那映着月光的眼睛,偏着头问我。
我反问道:“你呢?”
他把头微微向后摆了一下,说:“当然会。”然后又眨了几下眼睛,盯着我。我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比一比,行吗?看谁翻得快些。”他向我挑战了,我答应了。我刚翻到稻场中间,他就喊我停下,我直起腰来,看见他已站了起来,落后了一大截。我朝他走了过去,问道:
“怎么样?输了吧!”
他紧接着说:“不!你的手和脚隔得远些,我的手和脚隔得近些,你翻两个我要翻三个才跟得上。我们不比快慢了,比次数。”
我笑了,拍拍他的头对他说:“嗯,聪明!好!我应战,你先翻。”
他竟一口气翻了二十三个,我连连夸奖他不错。当然,最后还是他输了。
以后,我又搞了个篮球,举人也就成了我们知青篮球队的编外队员,他个头虽小,可不久也能十投七八中了。我发现他不光对体育很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很不错,语文算术常得100分,他还常常给我背当天在学校上的课文。虽然,下乡不到一年,我就考上了师范学院走了,但他那双眼睛我却一直没忘记。
上课外活动了,范进正在我寝室看书,我邀他同去打篮球。他皱了下眉头,拿着书跟我来到操场,我跟几个老师打起球来他站在场外看书。一会儿,我看见他在看我们打球,眼里闪着欲求的光。我喊道:
“举人,来吧!”
他望了望我,笑了笑,摇了摇头,低下头看书去了。我跑过去,夺过书,放在地上,抢过球,传给他,他竟没接住,又传给他,他才接住,可又没投中。
我问他:“你经常打球吗?”
他摇了摇头,轻声说:“还是读高一时上体育课,打过球,高二不上体育课。”
我奇怪了,课表上不是有体育课吗?举人告诉我那是怕上面来检查。我们正说着,范进突然放下手中的球,跑出场,飞快抓起书,低着头,走了。我一望,原来他的班主任余老师正怒目站在那边。
我正在洗脚,范进问我名词和分词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给他解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但又怕他上课没认真听,便问他上课为什么不问老师,他低声对我说:
“在初中没学过英语,上了高一就一直跟不上,有时即使问了老师,他也不认真解答。”
是啊,本来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可谁都知道,及格率只能看出老师的工作态度,尖子才能看出老师的业务水平。
在毕业生动员会上,刘主任作了自诩是实用主义的报告,他告诉同学们,说他们面临着草鞋和皮鞋,数工资和数公分,铁饭碗和泥饭碗的重要抉择。新溪一中孰不知,去年大中专共考取三十二人,这是历史最高纪录。据教务处最乐观的估计,今年最多能考上四十名。他接着说:
“同学们,这就是现实:有家刊物把高考比作独木桥上的竞争。的确如此,我们安能等闲视之?可时至今日,有极个别同学仍是米汤盆里坐,糊里糊涂过,还在打篮球!我说同学,你浪费掉的能简单地说是时间吗?不!那是你父亲一篾刀一篾刀从竹子里抢回来的命啦!你要珍惜,要发奋呃,如果再像去年名落孙山,我说你还有脸见你的父老吗?当然你会说,工农兵就不光荣吗?他们光荣。最近有这样几句顺口溜:五十年代土改根,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现在是一个大学生的时代!四化需要大批的大学生,而不需要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农民!”
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举人他受得了吗?他大概在流泪吧!也真怪,他竟没有哭,夹着书,低着头,来到我的寝室,叫了我一声,就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书,看起来多平静啊!此时他的心里一定像电影里出现的镜头一样,在翻腾,在狂啸!他忍受着多大的压力啊!十七岁应该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年龄,怎么会这样呢?
办公室里,朱老师正绘声绘色地向老师们介绍他改造后进生的经验。最近一次英语考试,文科复读班只有一个人没及格,朱老师去上课带了毛笔、墨、纸,在课堂上让那个学生当众写了“耻哉,不及格!”并叫那学生大声念了二十遍,直念得哭泣起来,又让这学生把这张纸挂在面前,站在讲台旁上了一节课。朱老师说以后英语课这学生必须挂这张纸。如果下次不及格,要挂上这纸条,在全校转几圈。好几个老师都叫起“妙哉”来。我问这学生叫什么,他顺口答道:“范进呗!”天哪,我赶快出了办公室,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宿舍。晚上我本想安慰举人一下,但一想反而不好,只是发现举人的头又低了一些。
这天该我值日,我去学生食堂维护进餐秩序。我看见范进站在队里,低着头,可能在回忆历史事件、地理现象或英语单词吧!吃饭的学生虽然不多,但挤得厉害。一个学生打了饭正往回走,被人一撞,一碗饭菜刚好泼在范进的身上。范进脸红了,嘴里在说着什么,那个学生大声骂了起来:
“眼睛全瞎了吗?学习没劲,吃饭倒带劲!耻哉,不及格!”
我看见范进低下了头,那么低,什么也没说。我的心猛一收缩,跑过去,拉过那个学生。他望了我一眼,竟甩手跑了。我眉头一皱,怎么如此没有礼貌?我几步跑上去抓住他,狠狠批评了一通。然后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程一兵。说完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学生们也奇怪地鸦雀无声了。
吃罢晚饭,我到办公室去路过教务处,听见高二文一班班主任宋老师正对主任高声说:
“主任,你应该知道,程一兵是新溪一中今年的一号种子选手,一块牌呀!铁平为何如此态度,马上就要预考了,这不是明摆着给学生精神上施加压力吗?”
刘主任说:“铁平老师不代文科的课,不了解情况,在目前这种吹糠见米的关键时刻,还是求大同存小异为好!”
我听不下去了,猛推开门,高声说:“求何大同?存何小异?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你倒还说强者有理,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宋老师忽地站了起来说:“我的逻辑!请你把程一兵和范进放在高考这架天平上称一称,看天平往哪头偏!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是为四化培养有用之才的问题。”
“好一个有用之才!不敬师长的有用之才!欺凌弱小的有用之才!你长期这样溺爱他,将来他会连你也不认的!”
“我不需要他认!只要他能考上大学。”
“只要他能考上北京大学,成为冯大兴第二也行,是吗?”
为此事,我不免受到高二文科班老师们的冷嘲热讽。从此,举人的头更低了,一天难说一句话。眼里少时的灵光全然消失了,有时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叫他好几遍,他才会问一声:“叫我吗?”
离预考只有一周了,举人几天来一直说头昏昏沉沉的。一天晚上,十点钟了,我劝他去睡觉,他说第二天要大考。的确,他怎能不急呢?大考六门功课都要考,考后排名次,成绩张榜公布,油印通知家长。上学期他还有点希望,总还可以搞个文科十一、二名,可这学期不行了,上次大考据说已降到三十八名了。想到这儿,我就先睡了。
我一觉醒来,天就亮了。啊,不是天亮了,范进还在看书!我一看手表,四点十分了,我赶快催他去睡觉。随后我去上厕所,看见他还站在去厕所的路灯下看书。我急了,跑过去,抓过书。他先是一愣,一看是我,就低下了头,我不由得心中一酸,还是送他去睡了。
离预考只有一周了,范进还在说头痛。医院一检查,严重神经衰弱!问题严重了,我没敢告诉他,也没敢告诉别人!怕他被取消预考资格就更加麻烦了。我估计他预考通不过,不如预考后再说。
预考榜揭晓了,举人落榜了。晚上他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学生宿舍为他送行,他正在默默地收拾行李。我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望着我,面部肌肉动了一下,大概是想笑,可又没笑出来。我递给他四本小书、一个笔记本,轻声说:
“这些送给你!”
“不必了,老师。”他叹了口气,答道。
“你看看吧!”我把书和笔记本塞到他手里。
他看了一下,一本《木耳栽培》,一本《蚯蚓饲养》,一本《青春书简》,一本《他们是怎样走上人生之路的》,笔记本上写着两句赠言:
叮咚的山泉也是一首诗
蓝天白云也是一幅画
他抬起头,眼里闪了一下光亮,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可泪水却在话之前流了出来……
我把他送上公路望着他走了。一个一个幻境闪现在我的眼前……
范进走进我的宿舍,递给我一大包木耳,脸上带着青春的笑容,眼镜后的眼里闪着少时的灵光,对我说:“铁平老师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现在我家是木耳万元户了……”
在街上,人们追赶着去看疯子,我挤进一看,是范进!他又去复读,可还是没考取,他疯了。把一块白胶布贴在衣服上,上面写着“北京大学”,一边走,一边唱“五十年代土改根,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呃……”
在河边,警察正对一具尸体拍照,很多人在围观,我去一看,是范进!他全身湿透,大概刚从河里捞起来,手里捏着一张纸条,大概是遗书,我拿来一看,是一首诗:
我劝世人莫读书
……
我两眼昏黑,两耳轰鸣,两手冰凉,两腿麻木,两脚沉重。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望见范进已背着行李,渐渐远去。他那低沉的头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此时我的喉咙像火烧一样,想喊,高喊,扯破嗓子喊,虽然我是个小人物,其喊声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还是要借用鲁迅先生的话高喊:
救救孩子!
山在应,水在应,树在应,云在应,连大气也在应:
孩子……孩子……
诗意语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