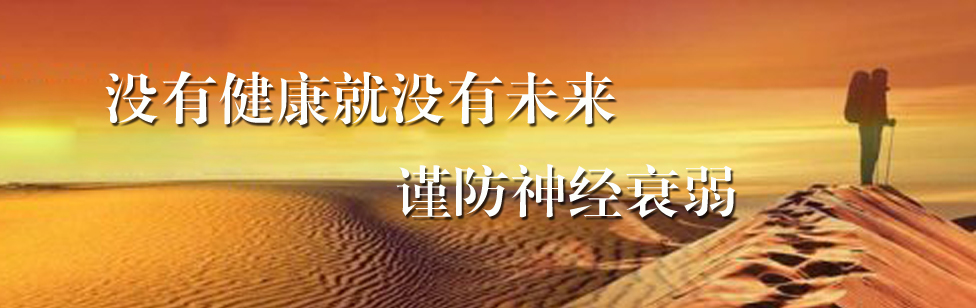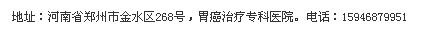陈赛那天,单位派豆子去博洛尼亚,一座美丽的意大利小城,参加一场美丽的童书展。这本来是每一个童书编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据她事后分析,一种有负众望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她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这是她很喜欢的工作,也是她能够胜任的工作。她喜欢孩子,喜欢故事,大学时毕业论文写的是《长袜子皮皮》。但她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工作的压力渐渐变得难以承受。
渐渐的,晚上不睡觉,吃不下饭,上班上一天,什么都写不出来,基本上处于怠工状态。每天给不同的朋友打电话,处于一种极度的倾诉状态。有一天,她给弟弟打了36个电话。
她本来是一个很开朗、很负责任的女孩子,这种转变自然遭到了很多怀疑的目光。公司以为她是想跳槽,同事开始指责她的不负责任。她的自我怀疑也越来越深:“一开始,别人指责你的时候,你觉得很气愤。很多人指责你的时候,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是不是真的挺自私的?”一个礼拜里,她瘦了10斤。她最后还是去了博洛尼亚,并在那里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至此,“抑郁症”这个词还从未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除了真正的抑郁患者外,没有人可以了解抑郁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张进,财新传媒副主编,在他自己的抑郁症笔记《渡过》一书中引用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一段描述:“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melancholia)的时候。”张进回忆道:“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12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这种时候,劝是没有用的。劝一个抑郁症患者“别多想”,就好像告诉一个皮肤烫伤患者,你别觉得疼一样徒劳。
当豆子的家人终于决定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处于呆滞状态,两眼无神,每天只做一个事情,拿着手机看电视。网络一断,立马要跳楼。“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有的亲戚都来跟我聊天。但任何事情都激不起我的兴趣。”“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活着有没有意义,而不是我这样想,是病态的,还是正常的?直到我真的好了,对生活有希望了,吃饭也香了,也想念周围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这样想,原来那段时间我是生病了。”当豆子从疾病中走出来,她仍然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会生病?正常的悲伤与病态的抑郁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悲伤与疾病的边界?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抑郁症最初的了解来自张国荣。那是很多人都记忆犹新的事情。年4月1日,这位受尽万千宠爱的明星从一座大饭店的高楼上高坠死亡。早在年,张国荣就在自传中写道:“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一种严重到会让人自杀的病。但是,与癌症不同,抑郁症并没有明确、可量化的病理诊断,连最先进的核磁共振都不能作为诊断或者排除的依据。祝卓宏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告诉本刊:“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真正符合‘疾病’的标准。因为一种‘疾病’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位、定性、病理特征,但‘精神疾病’无法满足其中任何一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说‘精神疾病’,而说‘精神障碍’)。比如,除了大脑里的神经系统之外,肠道里的细菌、微生物、菌群的变化也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么,‘精神疾病’到底应该定位在哪里?连精神分裂症也不能定位在大脑。《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报道的一个个案,就是讲一个人有被害妄想,在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结果是肠道对乳糜敏感。不吃乳糜,幻觉就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抑郁症更像是“发烧待查”,一个人发烧了,但未经检验,并不知道发烧的原因是什么。即使最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也只能依靠问诊,根据症状的表象,得到主观性的判断。比如,医院(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级医院)的杨甫德院长非常详细地向我解释抑郁症的三个核心症状:第一是情绪低落,完全处在悲伤中,任何事情都带不来快乐。其次是兴趣减退,尤其是过去很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再次是身体疲乏,哪怕一天无所事事,依然感到四肢疲软无力。第二是严重程度。正常的心情低落和抑郁症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工作能力和社会功能有没有受到损害。一般来说抑郁症中度以上,病人的学习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严重下降。但一个人心情不好,在能力损害上并不大。第三是持续时间。持续两周的心情低落就是抑郁症症状。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人有家族遗传史,有生物学基础,从小个性孤僻;还有一部分则是后天遭受了大的打击,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部分,家庭因素有一些,没那么重,没有遗传史,个性有一点缺陷,又遭受了大的打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的结果。虽然都同意“精神障碍是生物心理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医生对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解释却有着很大的分歧。杨甫德院长认为:“抑郁症发病的根本因素还是生物学因素,比如,可能有遗传因素、脑部结构的损坏,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至于发病能不能痊愈、什么时候痊愈,就是这些外界因素影响的,这些外界因素叫社会事件因素,当然也可能有个人性格因素。”但祝卓宏教授认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塑造十分重要,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更大。即使是大脑本身,也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一直在改变。现在(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一部分有易感基因(抑郁症基因),但更多的患者不因为生物学因素,而是后天经历了一些打击。”
“‘痛苦’这两个字的中文构成很有意思。”他说,“‘痛’是病字框的,是身体有病,而‘苦’是草字头,是一堆草的意象。苦像乱草一样,一茬一茬,不断滋长。也就是说,痛是身体有病感受到的,是有机体的反应,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苦是我们对事物的评价带来的,是你的态度带来的,是可以改变的。”他专攻心理治疗中一个叫“接纳承诺疗法”的流派,其核心概念“正念”,就是主张观察而不评价、不思考,只是用眼耳鼻舌身去感知世界、觉知世界,也不用语言、思维去思考世界、评价世界。他认为,从认知层面来说,“思维反刍”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抑郁症患者倾向于不断反思负性的东西,自动化的负性思维。抑郁症:一种陌生的疾病体验在一本题为《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的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到美国药厂葛兰素史克是如何在一个漫长痛苦的经济衰退时期,通过各种市场营销手段把抑郁症“推销”到日本的,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利益的推动之外,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科技。作者伊森·沃特斯指出,人类的绝大多数文化中确实有一种普遍的心境状态和一系列的行为,与失落或者失去他人有关,或是丧失了社会身份或个人动力。但同时不同文化对上述的存在状态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容和理解。比如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的这种,在文化上就是很特殊的。他们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悲伤的感受,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即使在美国,关于悲伤与疾病之间的界限,也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按照DSM-IV(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诊断标准,若丧失亲人后抑郁症状持续不足两个月,则不诊断抑郁。但到了年,DSM-5中这一排除标准被移除了。亲人去世后如果抑郁程度也达到了抑郁症的标准,即两周以上也算。这一改动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回归抑郁症的根本——我们的情绪系统应对重大的“失去”,无论是失去工作、失去尊严、失去感情、失去亲人,都是一样的。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抑郁症的过度诊断,是将正常的悲伤疾病化,是药厂在制造病人。正如作者所说:“当一种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有关心理或疯狂的信念乘虚而入。”在中国,是否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呢?毕竟,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个社会而言,中国人对于精神痛苦作为一种重大疾病的体验依然是陌生的。“在中国,滥用药物或滥治疗的情况有没有?”医院(医院)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告诉我们,“但中国抑郁症的主要问题是诊断和治疗不充分,而不是过度诊断。”医院的抑郁症治疗中心从年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从原来的张床位扩张到张床位。“刚成立的时候,医院门诊和住院的患者70%?80%都是精神分裂症,但这个中心成立3年后,数字就有了明显变化,门诊和住院患者50%,甚至50%以上都是心境障碍。”“为抑郁症设置单独的科室,是近10来年中国精神医学的一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抑郁症治疗的社会需求是很大的。社会